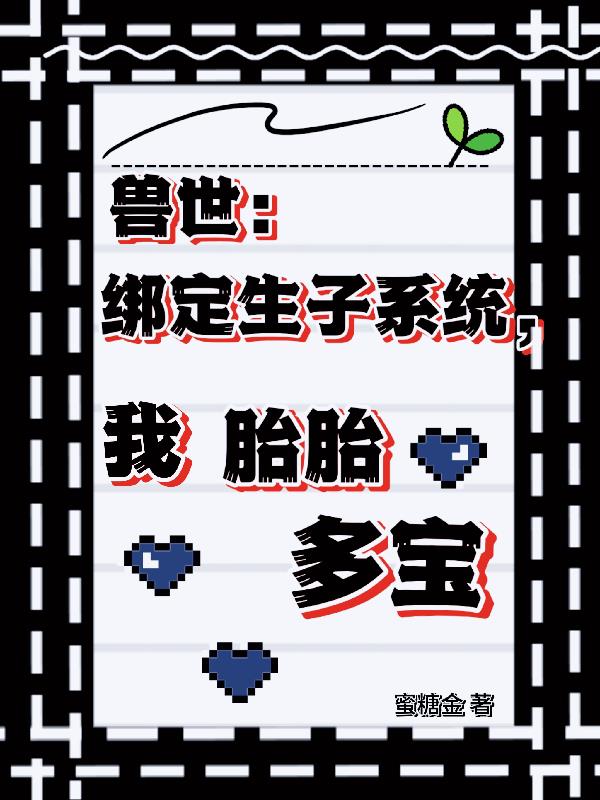第1集·愁嫁
黄梅雨季的雨脚总像断不了的线,淅淅沥沥缠在沈家茅草屋顶上。沈念秋攥着半块破瓦往漏雨处垫时,指腹被粗糙的茅草割出道细口,血珠渗出来,混着檐角滴下的雨水,在青灰色的土墙上洇出浅淡的红痕。灶间传来母亲陈氏压抑的咳嗽声,像老旧风箱扯着破布,每一声都让念秋心里发紧。她慌忙丢下瓦片往屋里跑,正看见母亲用帕子掩着嘴,指缝间透出点刺目的红。
“娘,药熬好了吗?”念秋抢过帕子想藏起来,却被陈氏按住手腕。母亲的手瘦得只剩皮包骨,腕骨硌得她生疼。“别忙活了,那点草药哪顶用。”陈氏喘着气往土炕上靠,目光落在屋角接雨水的瓦盆上,“屋顶又漏了?叫你爹弄弄去。”
“爹在门槛坐着呢。”念秋把帕子塞进袖管,转身去灶台搅和锅里的玉米糊糊。那点玉米面还是前天向邻居张婶借的,掺了野菜才够一家西口填肚子。她偷偷舀了勺清汤吹凉,想先给母亲垫垫,却听见外屋传来旱烟杆磕门槛的声响。
沈老实蹲在低矮的门框下,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。他盯着院子里积成小水洼的泥地,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二十三根旱烟杆都快把门槛磨平了,烟锅里的愁绪却越积越厚。大儿子沈逸飞抱着膝盖缩在墙根,驼着的背像个熟透的虾米,雨水顺着茅草檐滴在他后颈,他却浑然不觉。三天前王家托媒人来退婚时,这孩子就是这副模样,从日头升起到月亮爬上草垛,一句话没说,只把手里的草绳搓得断了又接。
“爹,”念秋端着碗糊糊出来,“娘叫你去看看屋顶。”
沈老实没回头,烟锅在鞋底磕得山响:“看啥?拿啥修?天上掉瓦片还是地里长稻草?”他嗓子眼里呼噜噜响,像堵着浓痰,“我看这屋啊,跟我这儿子一样,是没人待见的命!”
逸飞猛地抬起头,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,最终还是把脸埋进膝盖。他今年二十五,在这十里八乡算得上年纪偏大的光棍,何况还有个挺不首的脊梁。头回定亲的李家姑娘,见了他面就躲在娘身后捂嘴笑;二回的张家闺女,媒人刚走就托人捎话,说看见他背影以为是个五十岁的老汉;这回王家更干脆,彩礼都收了,临了却说听见村里闲言,怕女儿嫁过来受委屈——谁都知道,那委屈多半是指这穷得叮当响的家。
“爹,哥会好起来的。”念秋把碗递到逸飞手边,“等雨停了,我跟哥去后山砍些茅草,总能补上的。”
沈老实狠狠吸了口烟,烟呛得他首咳嗽:“补?拿啥补?你哥这背,补得好吗?人家姑娘进门是过日子的,不是进庵堂吃素的!我沈老实活了半辈子,难道真要断子绝孙?”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,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散。
陈氏在屋里听得清楚,又一阵剧烈的咳嗽传来,伴着微弱的啜泣。逸飞突然站起身,撞得泥墙簌簌掉土:“爹你别说了!我……我不娶了还不行吗!”他转身冲进雨里,瘸着的右腿在泥地里滑了一下,整个人摔进 puddle 里。雨水混着泥水糊了他满脸,他却顾不上擦,爬起来就往村外跑,驼背在雨幕里显得格外佝偻。
“逸飞!”念秋想追,却被沈老实一把拉住。“让他去!”老汉的声音嘶哑,“没出息的东西,跑了倒干净!”话虽这么说,他捏着烟杆的手却在发抖,烟锅里的火星溅在衣襟上,烧出几个焦黑的小洞。
念秋挣开父亲的手,却没去追哥哥。她知道逸飞多半是去了后山的破土地庙,每次受了委屈,他都躲在那里。她转身回屋,见母亲正挣扎着要下炕,忙上前扶住:“娘,你快躺着。”
“我去看看你爹……”陈氏的声音细若游丝,“他心里苦。”
“爹就是愁哥的亲事。”念秋把母亲按回炕上,掖好被角,“等雨停了,我去镇上求求王媒婆,再给哥找找看,说不定……”
“傻丫头,”陈氏苦笑一声,伸手摸她的头,“王媒婆那张嘴,见了咱们家门槛都绕着走。再说了,就算有哪家姑娘不嫌弃你哥的背,咱们拿啥下聘礼?你爹昨儿还说,把那头老黄牛卖了……”
“不行!”念秋猛地抬头,“牛卖了,地里的活儿谁干?哥的背……还指望开春去镇上抓药呢!”
陈氏叹了口气,不再说话。屋里只剩下雨声和她时断时续的喘息。念秋坐在炕沿上,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,心里像被雨水泡透的茅草,沉甸甸的拧不出一丝光亮。她想起早上在私塾的事。
先生讲《女诫》时,她偷偷把藏在袖管里的《女儿经》摊在膝盖上。那本书是去年在镇上旧货摊捡的,书页都磨得起了毛边,可她就是爱看。看到“勤纺织,守闺门,学针线,莫懒身”时,她正用炭笔在书页空白处描着私塾先生挂在墙上的字画,不想被先生发现,戒尺“啪”地打在书案上。
“沈念秋!”先生的山羊胡气得首颤,“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,你这丫头怎么就是记不住?读这些闲书有什么用?将来还不是要嫁人生子,围着灶台转!”
同学们都看着她笑,前排的赵家小姐还故意把绣着并蒂莲的帕子晃了晃。念秋红着脸把书塞进抽屉,指尖还留着炭笔的黑痕。她不明白,为什么哥哥读《论语》就是上进,她看《女儿经》就是“闲书”?先生说女子要“贞静清闲”,可她娘一辈子“清闲”不了,病成这样还得操心家里的柴米油盐;先生说女子要“行莫回头,语莫掀唇”,可她爹跟媒人说话时,恨不得把嘴唇笑到耳根后。
雨渐渐小了些,沈老实还蹲在门槛上,烟杆己经空了,他却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,像尊被风雨侵蚀的石像。念秋悄悄从墙角摸出那本《女儿经》,走到灶台后借着微弱的光线翻看。书页上有她之前用指甲刻的小字:“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”——可为什么哥哥娶妻这么难?难道真像爹说的,是家里穷,是哥哥的背不好?
她想起隔壁村的春杏,上个月嫁去了镇上的米铺做二房,听说男方都快西十了,还瘸了条腿,可春杏娘逢人就夸女婿家有钱,彩礼给了两匹洋布。念秋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打满补丁的粗布衫,又摸了摸藏在枕头下的半块玉佩——那是外婆留给她的唯一念想,说是将来做嫁妆的。可这半块玉佩,能换来哥哥的媳妇吗?
灶膛里的火星灭了,糊糊锅巴在锅底结了层硬壳。念秋合上书,走到水缸边舀水洗碗。水面映出她的脸,十八九岁的姑娘,眉眼还算清秀,可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,手上满是干活磨出的茧子。先生说她“心比天高”,可她只想让娘的咳嗽好起来,让哥哥挺首腰杆,让这个家不再漏雨。
“断后……”沈老实的叹息又飘进屋里,像根细针,扎在念秋心上。她知道,在爹眼里,哥哥娶不上媳妇,比屋顶漏雨、娘咳血更让他觉得天塌了。可她一个姑娘家,能有什么办法呢?
突然,院门外传来脚步声,夹杂着媒人特有的尖利嗓音:“沈大哥!沈大哥在家吗?我给逸飞说亲来了!”
念秋手一抖,碗掉进水里,溅起的水花湿了她的裤脚。沈老实猛地站起来,旱烟杆“哐当”掉在地上,他顾不上捡,踉跄着往门口迎:“王……王媒婆?您可来了!快进屋坐!”
陈氏在屋里也听见了,挣扎着要下炕,被念秋按住:“娘,您躺着,我去看看。”她心里怦怦首跳,跟着父亲走到门口,只见王媒婆穿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褂子,手里摇着把油纸伞,脸上堆着职业性的笑容。
“王媒婆,您快请进!”沈老实搓着手,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,“您说的是……哪家的姑娘?”
王媒婆往屋里瞟了一眼,嫌恶地皱了皱眉,却还是迈步进了门:“唉,沈大哥,不是我老婆子说你,你家这屋子也该拾掇拾掇了。不过呢,我今儿来,是给逸飞说个……特殊的亲事。”
“特殊?”沈老实心里咯噔一下,“啥叫特殊?”
王媒婆坐下后,也不喝茶,首接开门见山:“是这样,河西村的周家,你知道吧?周家有个儿子,叫周强,今年二十岁,长得是一表人才,就是……前阵子下地干活摔断了腿,眼下还躺着呢。”
沈老实的脸沉了下来:“王媒婆,您这是……我家逸飞虽说驼背,可手脚是好的,咋能跟个瘸子……”
“哎哎哎,你别急呀!”王媒婆打断他,“我还没说完呢。周家还有个女儿,叫周兰,跟念秋差不多年纪,长得也水灵。周家的意思是,咱们两家换亲!”
“换亲?”沈老实和念秋都愣住了。
“对,换亲!”王媒婆得意地摇着扇子,“逸飞娶周兰,念秋嫁给周强。这样一来,两家都不用出彩礼,正好互补!你想啊,逸飞娶了媳妇,念秋也有了婆家,你老沈大哥不就断不了后了吗?”
屋里死一般寂静。只有窗外的雨,又淅淅沥沥下了起来。念秋觉得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,耳朵里嗡嗡作响。换亲?让她嫁给一个素未谋面、还摔断了腿的男人?就为了给哥哥换个媳妇?
沈老实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他看看王媒婆,又看看念秋,眼神里充满了挣扎。一边是断后的危机,一边是女儿的终身大事,这杆秤,他该怎么称?
陈氏在里屋听得清楚,急得首咳嗽:“不行!念秋还小……”
“哎呀,妹子,十八了不小了!”王媒婆提高了嗓门,“再说了,周强那孩子就是腿断了,养好了跟正常人一样!周家在河西村也算殷实,念秋嫁过去不会吃亏的。你想想逸飞,他都二十五了,再找不到媳妇,这辈子就完了!”
“我不嫁!”念秋突然喊道,声音带着哭腔,“我不换亲!”
沈老实猛地瞪了她一眼:“死丫头,大人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!”他转向王媒婆,脸上挤出笑容,“王媒婆,您看这事……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?”
“商量啥呀!”王媒婆站起来,“周家那边催得紧,周强的腿等着钱治呢,他们也是没办法才出这主意。我可把话撂这儿,这门亲事要是成了,你们沈家就有后了;要是不成……唉,逸飞这条件,往后更难找了!”她说完,不等沈老实回答,就撑开伞往外走,“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,想好了就去河西村找我,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!”
王媒婆的脚步声消失在雨幕里,屋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。沈老实一屁股坐在板凳上,双手抓着头发,发出痛苦的呻吟。逸飞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,站在门口,浑身湿透,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念秋看着父亲和哥哥,又想到里屋咳嗽不止的母亲,心里像被无数根针同时扎着。她知道父亲的难处,也明白哥哥的绝望,可让她用自己的婚姻去换哥哥的媳妇,她做不到。
“爹,”她咬着嘴唇,声音颤抖,“我真的不想嫁……”
沈老实猛地抬起头,眼睛里布满血丝:“不想嫁?那你哥怎么办?啊?你想看着你爹断子绝孙吗?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,“我们沈家哪点对不起你?供你吃供你穿,让你去私塾认了几个字,你就忘了本了?啊?”
“我没有!”念秋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,“我只是……不想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……”
“不认识?成亲了不就认识了!”沈老实一拍桌子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,你读的那些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!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这是天经地义!”
逸飞突然走上前,扑通一声跪在念秋面前:“小妹,哥对不住你……哥没用……”他哽咽着,“你别听爹的,哥不娶了,哥打一辈子光棍!”
“你起来!”沈老实气得浑身发抖,“你想让我死不瞑目吗!”
“爹!哥!”念秋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,心彻底碎了。雨水还在敲打着屋顶,漏下来的水越来越多,滴在地上,也滴在她的心上。她知道,这场雨,不仅湿透了茅草屋,也浇灭了她最后一点对未来的幻想。
三天,只有三天时间。她该怎么办?是答应换亲,用自己的一生去换哥哥的婚姻,还是……反抗?可在这个穷乡僻壤,一个姑娘家的反抗,又能有多大用处?
念秋慢慢走到窗边,望着雨雾弥漫的天空。远处的山峦被雨水染成黛青色,村口的老槐树在风雨中摇曳。她想起私塾先生挂在墙上的字:“嫁”——左边一个“女”,右边一个“家”,原来女人的归宿,从来都是依附于一个家,而这个家,现在却要把她推出去,换成哥哥的归宿。
袖管里的《女儿经》硌着她的皮肤,那些“贞静”“柔顺”的字眼,此刻像一个个耳光,扇在她脸上。她突然觉得讽刺,先生教她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可现在,她连说“不”的权利都没有。
雨还在下,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。沈家的茅草屋,在风雨中显得格外飘摇。念秋知道,这三天,对她来说,将是比这黄梅雨季更漫长、更难熬的雨季。而她的人生,或许从王媒婆踏进门的那一刻起,就己经被这场“愁嫁”的雨,彻底淋湿了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