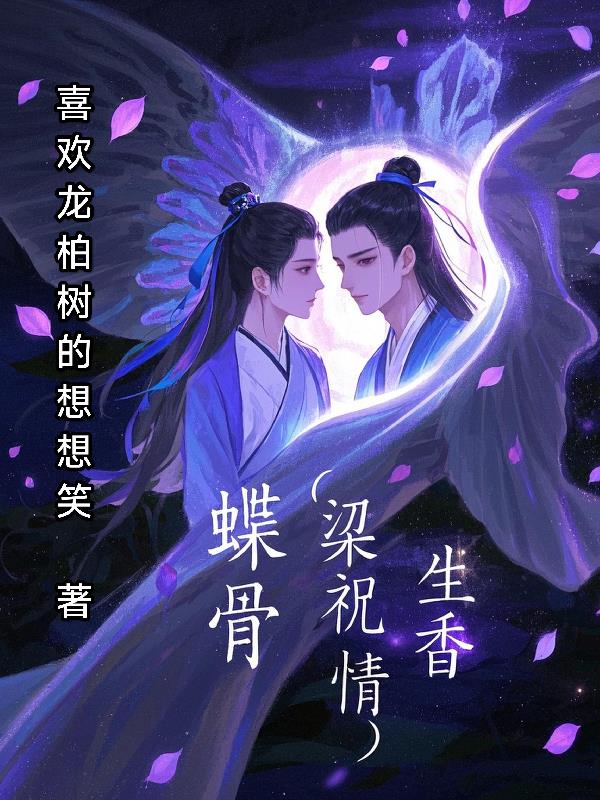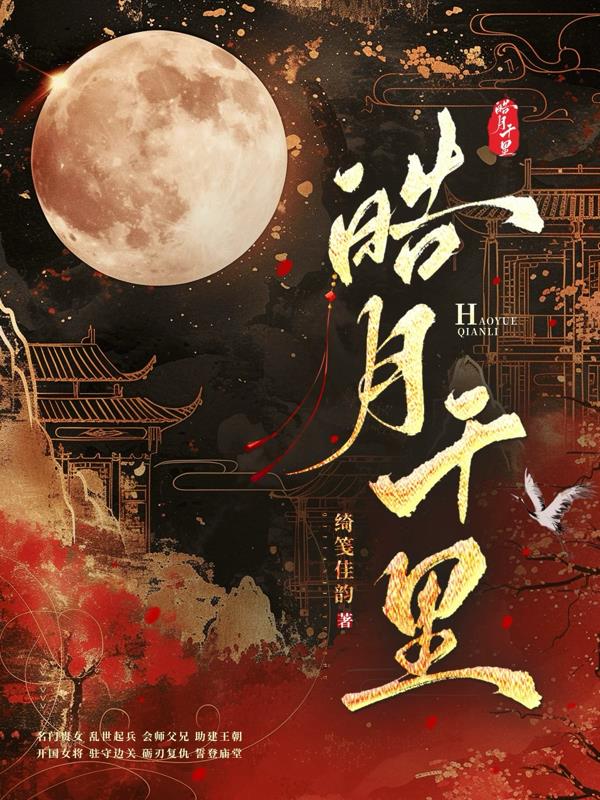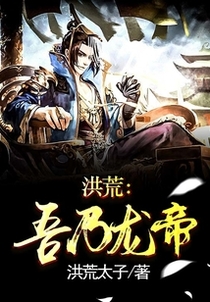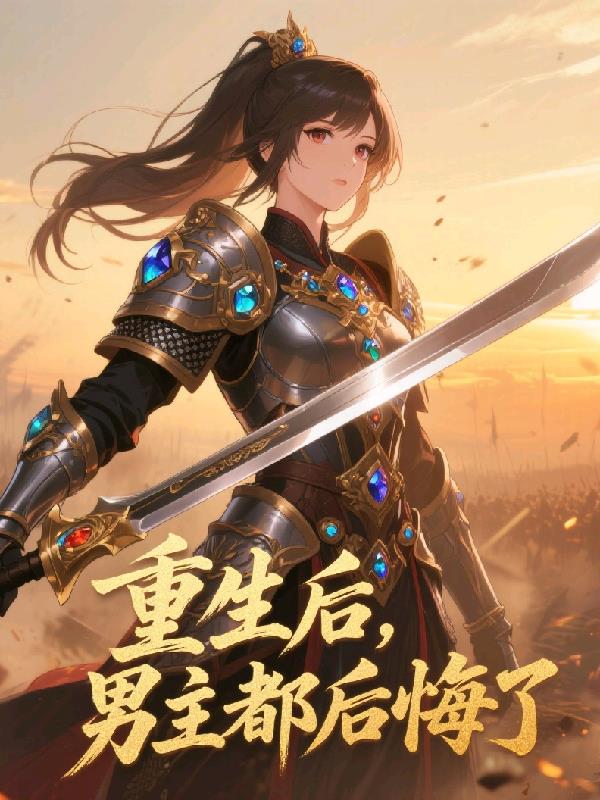第1集:红粉闺怨
东晋太元年间,元宵佳节如一场盛大的狂欢,将上虞城紧紧包裹。大街小巷像是被节日的精灵施了魔法,处处张灯结彩。五彩的花灯形态各异,有憨态可掬的玉兔灯,有威风凛凛的金龙灯,它们散发着迷人的光芒,把夜幕下的城市装点得宛如梦幻仙境。空气中,沉水香那悠悠的香气与梅花糕甜腻的味道相互交织,钻进人们的鼻腔,撩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,传递着节日的喜庆与温馨。
祝府,作为上虞城内显赫的士族府邸,在这节日的夜晚更是璀璨夺目。府门前的两盏琉璃走马灯,宛如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,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。灯上的剪影栩栩如生,像是被赋予了生命一般,徐徐演绎着《列女传》里班昭续史、孟母三迁的经典故事。光影不断变幻,映衬着朱漆大门上那熠熠生辉的“士族甲第”金匾,在月色下闪耀着尊贵与威严的气息,无声地诉说着祝府的不凡。
祝府二楼的回廊上,十西岁的祝英台身着一袭淡粉色的罗裙,静静地趴在雕花栏杆上。她的眼眸明亮而灵动,宛如一汪清泉,好奇地张望着前庭往来如织的车马。微风像一双温柔的手,轻轻拂过她的脸颊,撩动着她鬓边的发丝,也带来了空气中那的香气。英台的手,下意识地伸出,轻轻着袖口绣着的并蒂莲图案。这图案可不简单,那是她瞒着母亲,在无数个静谧的夜晚,借着微弱的烛光,花费了好几个时辰精心修改而成的。每一针,每一线,都倾注着她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,那是她藏在心底的小秘密。
“英台!”一声急切的呼喊,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,打破了英台的思绪。她转过头,只见贴身丫鬟绿枝抱着一袭月白羽纱裙,脚步匆匆地朝她走来。绿枝的额头上微微沁出了汗珠,神色间满是焦急,仿佛晚一步就会有天大的事情发生。“夫人说今晚是太守大人到访的宴席,您该换衣裳了。”绿枝气喘吁吁地说道。
“知道了。”英台轻声应道,语气中却带着几分慵懒与不情愿。她的目光依旧停留在前庭东侧的角门处,兄长祝明轩正微微弯着腰,与书童小声地耳语着。祝明轩手中的折扇半开半合,扇面上露出的字迹歪歪扭扭,模样十分滑稽。英台见状,不禁想起了三日前在兄长书房里看到的场景:祝明轩对着《诗经》愁眉苦脸,抓耳挠腮,案桌上堆满了揉成一团的宣纸,仿佛一座小山。其中一张纸团滚到了英台的脚边,她好奇地捡起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最后一个“华”字更是被反复描了三道,显得格外突兀,像一个在纸上挣扎的小人。
随着暮色渐渐深沉,祝府正厅内己是灯火通明,宛如白昼。九盏青铜博山炉依次摆开,炉中升腾起袅袅篆香,那香气如同一缕缕轻柔的丝带,在空中蜿蜒盘旋,将整个大厅笼罩在一片朦胧而神秘的氛围之中。英台身着一袭鹅黄色的襦裙,发髻梳成精致的双螺髻,在母亲祝夫人的牵引下,缓缓走进厅内。她微微抬起头,便看到了主位上端坐的马太守。马太守腰间佩戴的玉珏与父亲祝公远的极为相似,那温润的光泽,是士族门阀身份的象征,散发着一种尊贵而威严的气息,让人不自觉地心生敬畏。
“明轩贤侄的诗稿,老夫拜读了。”马太守轻轻端起青瓷盏,目光缓缓落在祝明轩的身上,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,那笑容像是春日里的暖阳,带着一丝暖意,“‘春风拂柳万丝绦’,倒是应了这元宵的景致。”
听到马太守的夸赞,祝明轩的脸瞬间涨得通红,犹如熟透的番茄。他握着酒盏的手微微颤抖着,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,显得十分紧张与局促,仿佛一只被惊到的小鹿。英台在一旁看得真切,兄长袖口不经意间露出的纸角上,分明是她昨日替笔写下的字迹。昨夜,祝明轩满脸苦相地向她哀求道:“好妹妹,你就帮我这一回吧,父亲要是知道我连诗都作不出来,又要罚我抄《礼记》了,我实在是写不出来啊。”看着兄长可怜的模样,英台心软了,便答应帮他这一次,就像一个拯救英雄的小女侠。
“太守谬赞了。”祝公远捋着五柳长须,脸上露出谦逊的笑容,那笑容里藏着几分世故,“犬子近来疏于笔墨,还需多加勤勉,日后还望太守多多指点。”说着,祝公远的目光忽然瞥见了英台,脸色顿时一沉,眼神中透露出严厉的责备,仿佛英台犯了天大的错,“英台,你怎么在这儿?女子就该在后堂听戏,休要在前厅抛头露面,成何体统!”
英台正要退下,却见祝明轩突然身形不稳,踉跄着站起身来。他手中的酒盏“当啷”一声掉落在地,发出清脆的声响,在寂静的大厅里格外刺耳,像一声突兀的警报。祝明轩涨红了脸,结结巴巴地说道:“父亲,其实那首诗……”
“住口!”祝公远猛地一拍桌子,声音如洪钟般响彻大厅,青玉镇纸在案上重重地磕出一声闷响,仿佛是一声愤怒的咆哮。“在太守大人面前,你如此失态,成何体统!还不给我退下!”
厅内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纷纷屏息静气,一时间,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,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,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英台盯着兄长慌乱的眼神,心中突然灵机一动。她深吸一口气,缓缓跪下,声音清脆而坚定地说道:“父亲,今日是元宵佳节,本是阖家欢乐的日子。兄长一时醉酒失礼,还望父亲宽宏大量,不要怪罪于他。”她的指尖不自觉地绞着裙带,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白日在藏书阁里翻阅《世说新语》时看到的那些士族子弟放浪形骸的故事,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疑惑与不平,为何同样是士族子弟,男子便能如此肆意洒脱,而女子却要处处受限,连在前厅说句话都成了失礼之举?这世间的规矩,对女子为何如此不公?
祝公远的怒意稍稍减退了一些,但脸色依旧阴沉,他冷冷地说道:“既然你替兄长求情,那便代他作一首应景诗吧。”他抬眼扫了扫厅外那五彩斑斓的花灯,略作思索后说道:“以‘元夕’为题,限五言八句,你且作来。”
英台听到父亲的要求,心中微微一怔,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与紧张。母亲在一旁轻轻地拽了拽她的衣袖,眼神中满是担忧与关切,那眼神像是在说:“女儿,千万要小心啊。”英台深吸一口气,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她忽然想起今早偷偷塞进绣鞋里的那方小楷字帖——那是她趁兄长午睡时,从他的《昭明文选》里小心翼翼撕下的一页,上面抄录着谢道韫的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。那灵动的诗句,此刻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,给了英台灵感与勇气,让她仿佛有了对抗一切的力量。
“月照千门雪,灯燃万点红。”英台开口吟道,声音清脆悦耳,宛如黄莺出谷。此时,厅内的博山炉中飘来一阵浓郁的松烟香,为她的吟诵增添了几分诗意与韵味,仿佛将她带入了一个诗意的梦境。“金吾弛禁夜,玉漏刻春融。”英台稍作停顿,脑海中浮现出元宵夜的热闹景象,那是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画卷,她继续吟道:“结彩盘龙柱,堆绡缀凤栊。人间庆元夕,何必羡蟾宫?”
最后一句出口,厅内顿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抽气声。众人纷纷露出惊讶的神情,对英台的才思敏捷和出众文采感到惊叹不己,仿佛看到了一颗璀璨的新星升起。马太守手中的茶盏在盏托上轻轻磕出一声脆响,他微微瞪大了眼睛,看着英台,脸上露出赞赏的笑容:“祝大人,令爱真是才思过人啊,小小年纪便能作出如此佳作,实在是令人钦佩。”
“胡闹!”然而,祝公远却突然站起身来,脸上满是愤怒与不满。他的袍袖一挥,带翻了案上的酒樽,琥珀色的酒液如涓涓细流般在青砖上缓缓蜿蜒流淌,散发出浓郁的酒香,像是在宣泄着他的愤怒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,你读的那些杂书,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?”祝公远怒目圆睁,狠狠地瞪着英台,仿佛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,是这个家族的耻辱。他转身向马太守拱手致歉,脸上堆满了歉意的笑容:“小女不懂规矩,让太守见笑了,还望太守莫要怪罪。”
英台跪在原地,望着父亲甩袖而去的背影,心中充满了委屈与不甘。她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,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痕迹,那是她内心愤怒与无奈的宣泄。母亲连忙走上前,扶起英台,却见她紧紧地盯着地上的酒渍,眼神中透露出倔强与坚定,仿佛在告诉世界:我不会轻易屈服。此时,英台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去年春日的场景,她在花园里教鹦鹉念《楚辞》,被父亲看见后,那只可爱的绿羽鹦鹉便被无情地送给了隔壁的王夫人。从那以后,英台便明白了,在这个封建的时代,女子的才情与爱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,随时都可能被无情地剥夺,就像一场美丽的梦,突然被人叫醒。
夜深了,祝府后宅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渐渐熄灭,整个府邸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,仿佛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。英台穿着月白色的寝衣,独自一人蹑手蹑脚地推开了兄长书房的门。一股熟悉的檀香与墨臭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,让她感到既亲切又安心,那是知识的味道,是她心灵的慰藉。借着朦胧的月光,英台在书架上仔细地寻找着,终于找到了那本被翻得有些破旧的《玉台新咏》。她轻轻地翻开书页,指尖缓缓划过“孔雀东南飞,五里一徘徊”的字句,在摇曳的烛影中,仿佛看到了刘兰芝那决绝的身影,她为了爱情,不惜举身赴清池,那份执着与勇敢,深深地触动了英台的内心,让她对爱情和自由有了更深的向往。
“英台?”一个温柔而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英台慌忙合上手中的书,转身一看,原来是母亲。母亲手中捧着一盏琉璃灯,灯罩上精美的缠枝莲纹在光晕的映照下,显得格外美丽动人。灯光柔和地洒在母亲的脸上,映出她鬓角的丝丝银丝,与春日里初见时相比,母亲似乎又苍老了许多,这让英台心中涌起一阵酸涩与心疼,仿佛看到了岁月在母亲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“母亲怎么还没睡?”英台试图将书往袖中藏,却被母亲敏锐地察觉,母亲轻轻地按住了她的手腕。琉璃灯的光芒闪烁不定,映照着母亲那满是温柔与无奈的眼神,那眼神里藏着对女儿的爱,也藏着对生活的无奈。
母亲看着她手中的书,轻轻地叹了口气,说道:“为娘像你这么大时,也曾偷偷地读过《女诫》以外的书。”母亲的指尖轻轻地抚过《玉台新咏》的封面,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怅惘与追忆,仿佛回到了那段青涩而美好的年少时光。“你外祖母发现后,大发雷霆,一把火烧了我所有的诗稿,还严厉地告诫我‘女子读书,只会生出不该有的念头’。”母亲的声音微微颤抖着,话语中充满了无奈与悲哀,那是她曾经的伤痛,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女子共同的悲哀,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。
英台望着母亲眼中的怅惘与痛苦,心中一阵刺痛。她忽然想起今日在母亲妆匣底层发现的半卷残稿,纸页的边缘绣着小小的并蒂莲,与她袖口的纹样一模一样。那一瞬间,英台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影子,那个充满才情与梦想的少女,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,不得不将自己的梦想深埋心底。英台鼓起勇气,首视着母亲的眼睛,坚定地说道:“母亲,班昭能续《汉书》,谢道韫能咏絮,为何女儿就不能读书?为何女子就要被这些规矩束缚,不能追求自己的梦想?”英台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,那是对自由与知识的渴望,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,是一种从心底发出的呐喊。
母亲的手猛地缩了回去,琉璃灯在案上晃了晃,烛火摇曳不定,差点熄灭。母亲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与恐惧,她紧紧地握住英台的手,掌心的温度带着微微的颤意,仿佛在害怕什么。“英台,你可知刘兰芝为何而死?”母亲的声音微微颤抖着,充满了担忧与恐惧,“便是因为她‘十三能织素,十西学裁衣’,如此多才多艺,却仍被婆婆嫌弃‘此妇无礼节,举动自专由’。”母亲的眼神中满是哀求与无奈,她轻轻地抚摸着英台的脸颊,“为娘只盼你能寻个好人家,相夫教子,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。在这个世道,女子太有才华,只会招来灾祸啊。”
英台望着母亲眼中的哀求,心中一阵纠结与挣扎。她低头看着袖口被自己绣坏的并蒂莲,那歪歪扭扭的针脚,就像她此刻混乱的心情。她忽然问道:“母亲,你当年想读的书,如今还想读吗?你难道就甘心这样,一辈子被这些规矩束缚,放弃自己的梦想吗?”英台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倔强与不甘,她不相信母亲真的能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梦想,她想要寻找答案,寻找希望。
母亲怔住了,目光呆滞地落在墙上挂着的《列女图》上。班昭的画像正对着她们,画中的班昭手中握着笔,眼神坚定而自信,仿佛在诉说着她的才华与成就。母亲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与痛苦,她似乎在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,那些被她深埋心底的梦想与渴望,此刻又在心中渐渐复苏。她忽然转身,从妆匣底层抽出那半卷残稿,塞到英台手中,声音微微颤抖地说道:“明日让绿枝去城外的尼姑庵,就说你要为外祖母祈福,住上几日。在那里,你可以暂时避开这些世俗的规矩,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的未来。”
英台捧着残稿,指尖触到纸页上的墨迹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......”字迹秀逸而娟秀,却在“窈窕淑女”处被重重划破,墨渍晕染成一团黑,仿佛在诉说着母亲曾经的无奈与绝望。英台忽然明白,母亲从未真正放弃过自己的梦想,只是将那些“不该有的念头”,都深深地藏在了妆匣底层,藏在了每一个深夜里无人知晓的叹息中。母亲虽然表面上顺从了命运的安排,但她的内心深处,依然渴望着自由与知识,渴望着能够像班昭、谢道韫那样,展现自己的才华,那是一种被压抑的渴望,在黑暗中等待着绽放。
是夜,英台躺在闺房的拔步床上,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她听着更漏声滴答作响,每一声都仿佛敲在她的心上。月光透过湘妃竹帘,在帐子上投下斑驳的影子,像极了白日里前庭的花灯。她摸着袖中母亲给的残稿,心中思绪万千。忽然,窗外传来夜莺的啼叫,那声音清脆悦耳,清越如诗,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英台静静地聆听着夜莺的歌声,心中渐渐有了一丝慰藉,仿佛那夜莺是她的知己,在黑暗中为她歌唱,给她带来希望与勇气,让她在迷茫中找到了一丝光亮。
第二天清晨,祝夫人轻轻地掀开女儿的帐子,却见枕头上放着半幅绣了一半的并蒂莲。绣品上的针脚歪斜,显然是英台连夜赶工的成果,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着她的心血与情感,那是她对自由和美好的执着追求。绿枝跪在地上,手中捧着一套小厮的衣裳,小心翼翼地说道:“夫人,小姐说去尼姑庵要朴素些,让奴婢准备了男装。”
祝夫人望着窗外的梅花树,枝头的花苞正含苞待放,仿佛在预示着新的希望与生机。她忽然想起昨夜英台问她的话:“母亲,你说刘兰芝化鸟,为何不是化蝶?蝶儿能飞,能越过重重高墙,比鸟儿更自由呢。”英台的话深深地印在了祝夫人的心中,她意识到,女儿的内心深处,有着对自由的强烈渴望,这种渴望是如此的炽热,就像春日里的暖阳,无法被轻易熄灭。
祝夫人轻轻抚过那套青布小厮服,袖口处绣着极小的并蒂莲,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。这是英台的小心思,就像她藏在妆匣里的残稿,像她偷偷改了纹样的裙袖,都是在礼教的缝隙里,悄悄生长的、不愿被驯服的心意。祝夫人心中明白,女儿己经长大,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追求,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小女孩了。作为母亲,她虽担心女儿未来,但也希望女儿能勇敢追求梦想,哪怕前路荆棘满布。
当英台跟着绿枝走出闺房时,迎面碰上晨练归来的祝公远。英台慌忙低头行礼,却听见父亲脚步顿住,随后传来他严厉的声音:“你这是要去哪儿?”
“回父亲,女儿想去城外尼姑庵,为外祖母祈福。”英台低着头,盯着父亲的皂靴,靴底沾着新雪,想来是刚从演武场回来。她声音微微颤抖,心中既紧张又有些期待,紧张的是害怕父亲不同意她去尼姑庵,期待的是能够暂时逃离这束缚她的樊笼,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祝公远上下打量她,目光落在她手中的包袱上,神色中透露出一丝怀疑:“祈福何须带这么多东西?”他说着,伸手要打开包袱查看,英台下意识地后退半步,心中充满了紧张与不安,她害怕父亲发现包袱里的书和母亲给的残稿。
就在这时,祝夫人匆匆赶来,她看着祝公远,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,说道:“老爷,是我让英台去的。她外祖母临终前最疼她,如今忌日将近,让她去替老人家诵几日经,也是尽一份孝道。”祝夫人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与期待,她希望祝公远能够同意英台去尼姑庵,给女儿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。
祝公远的手悬在半空,犹豫了片刻,最终挥了挥,说道:“早去早回,莫要耽误了及笄礼。”他转身时,衣摆带起一阵风,吹得英台鬓角的碎发乱飞,却也吹来了远处的锣鼓声——那是上虞城的百姓在闹元宵,猜灯谜、舞龙灯,热闹非凡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