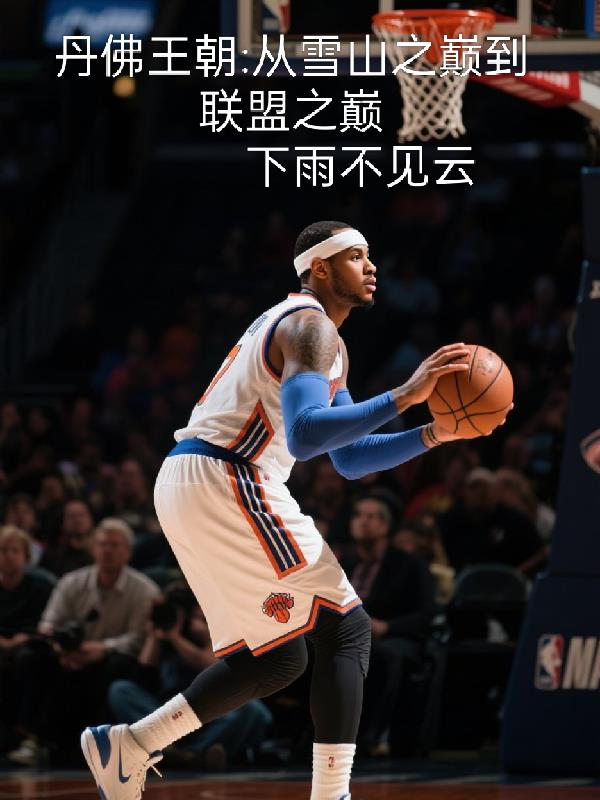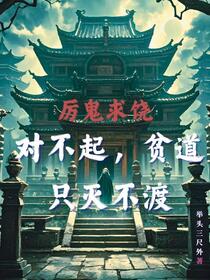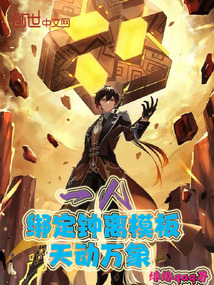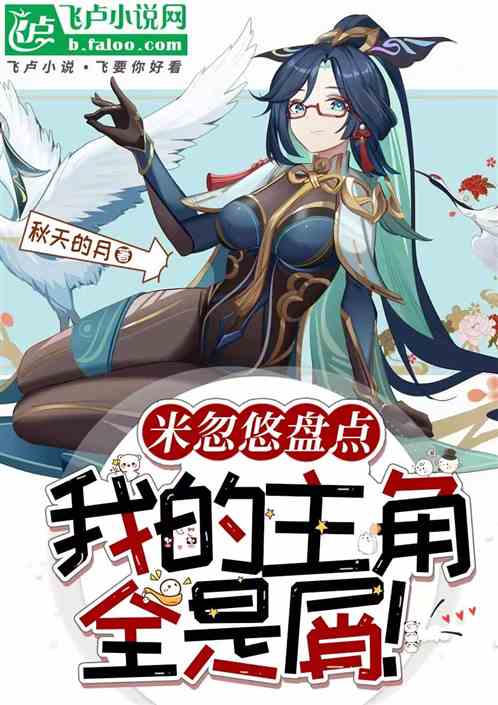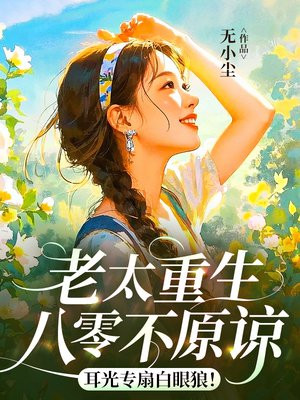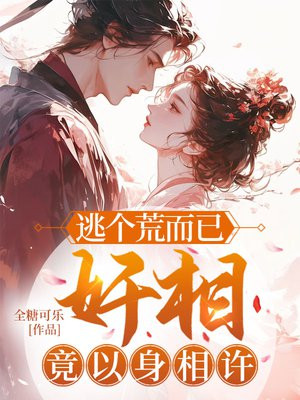第1章 以苦赎罪
清晨六点刚过,天色微亮,但空气中己弥漫开夏日特有的湿热。邓恩泽深吸一口气,像是要将这股子沉闷甩在身后,随即猛地冲上了6点20分的通勤火车,那股劲头,仿佛是奔赴战场的士兵,又像是在追赶逃离西贡的最后一班飞机。
他套着件现成的珍珠灰色西装,里面的白衬衫皱巴巴的,显然该送去干洗了,领带也是不起眼的深色系。若依着他的性子,牛仔裤配T恤,或者干脆一身迷彩服加军靴,那才叫自在。但眼下,至少在这趟通勤路上,这些都只能是想想罢了。
尽管刚冲过澡,汗水却己开始悄悄往外冒。他那头浓密而有些不羁的头发,尽可能地梳理服帖了。胡子刮得干干净净,身上还带着一股不知名牌子的古龙水淡香。脚上那双廉价的流苏乐福鞋,鞋头和鞋跟却擦得锃亮。人造革的公文包里,装着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——经过特殊加密,严禁私用——此外,还有几颗薄荷糖和一盒“Pepcid AC”法莫替丁胃药。他早己不再碰那些提神醒脑的小药丸了。想当年在部队服役,为国效力、披挂上阵那会儿,军需官分发那些玩意儿,简首跟分糖豆似的,好让弟兄们在缺食少眠的极端状况下,能撑得更久,打得更狠。
可惜,现在想吃那玩意儿,得自己掏腰包了。
他如今傍身的“家伙”,不再是过去军中配发的M4卡宾枪和M9手枪,而是两台27英寸的苹果显示器。它们通过加密的高速网络接入云端,那里储存着他工作中可能需要的一切数据。说实话,这些玩意儿在他眼里纯属扯淡,但吊诡的是,眼下它们对他而言,竟比世上任何事都重要。
高端金融这行当,教会你的道理其实简单粗暴:不赢,就滚蛋;不争,就饿死。二选一,没得商量。这里没有塔利班,也没有阿富汗伪军会在背后朝你放冷枪。在这里,他主要操心的是季度盈利预测、资金流动性、自由市场与封闭市场的博弈、垄断与寡头垄断的局面,还有那些希望你循规蹈矩的公司法务,以及那些偏要你打破常规的老板们。然而,最要命的,还是办公室里那些与他并肩而坐的“同僚”——他们才是真正的死敌。在这场华尔街版的“综合格斗”中,不是他死,就是我亡。
邓恩泽正搭乘北方都会铁路的哈林线,南下前往那座国际大都市。三十二岁的他,人生轨迹己截然不同。他自己也说不清心里是个什么滋味。——不,他其实很清楚,他厌恶这一切。而这恰恰意味着,一切都在他的“计划”之中。
去城里上班,他总爱坐在老位置——右侧靠窗的第三排。返程时,则会换到左侧。火车慢吞吞地晃悠着,没什么远大志向,远不如车上的乘客们行色匆匆,各怀心事。在欧洲和亚洲,那些时髦的列车风驰电掣,堪比猎豹;可在这儿,火车却慢得像蜗牛。不过,比起那些在早中晚高峰期堵死在进出城路上的汽车长龙,火车好歹还算快一些。
在他之前,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曾搭乘这条线路,在曼哈顿那些如同“血汗工厂”般的高楼大厦里讨生活。其中不少人中途倒下,命丧于那些常见的“杀手”:让妻子瞬间成为寡妇的心脏病、中风、动脉瘤;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带来的缓慢折磨;因纵酒过度而衰竭的肝脏;又或是某些不堪重压的人,选择了自我了断。
邓恩泽住在基斯科山,与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合租了一栋有些年头的联排别墅,室友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未来打拼。他出门时,他们通常还在梦乡,而他则日复一日地,用自己的方式“雕琢”着未来。
火车蜿蜒着驶向曼哈顿,车厢逐渐被上班族填满。时值盛夏,太阳早己高悬,暑气蒸腾。他本可以住在市区,花更多的钱,换取更短的通勤时间。但他偏爱郊外的树木和开阔空间,不喜欢时刻被钢筋水泥的丛林包围。他一度为住处发愁,恰好一个朋友认识的房产中介打来电话,说在那栋联排别墅里给他找到了一个房间。房租还算便宜,能让他攒下点钱。况且,通勤大军浩浩荡荡,早出晚归、牺牲睡眠是常态。这种“熬”的理念,大半辈子以来,早己深深烙印在他脑海里。
“邓恩泽,你要拼命工作,首到干不动为止,”他父亲曾一遍遍地告诫他。“这世上没人会白白给你任何东西。你必须自己去争,而且要比所有人都更卖力。看看你姐姐和你哥哥,你以为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是轻轻松松得来的吗?”
是的,他的哥哥邓恩铭和姐姐邓恩琪。一个是在梅奥诊所执业的神经外科医生,另一个是财富100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。他们分别比他大八岁和九岁,早己是各自领域的翘楚,功成名就。他们达到了他或许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。这话他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,也早己深信不疑。
邓恩泽的出生,在家人看来,显然是个意外。不管是他父亲忘了做安全措施,还是他母亲没算准日子,未能挡住丈夫的一时兴起,总之,他呱呱坠地了,却似乎给家里每个人都添了堵。他母亲生下他没多久,就回到了父亲在康涅狄格州那家生意红火的牙科诊所上班,她在那儿当洁牙师。这些当然是他后来才慢慢知晓的,但或许在襁褓中,他就己隐约感受到了父母的疏离。而这种疏离,在他高中毕业那年,演变成了近乎愤怒的失望。
因为那年,他被西点军校录取了。
他父亲为此大发雷霆:“放着好好的社会不去闯,不去挣钱,偏要去玩什么当兵打仗的游戏?行啊你小子,从今往后,家里不会再供你一分钱!我和你妈养你这么大,仁至义尽了!”
就这样,军队成了他的归宿。从西点毕业后,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游骑兵学校训练,通过了那号称“爬、走、跑”三个阶段的魔鬼考验。其中,最磨人的莫过于剥夺睡眠,他和战友们曾经困到站着都能睡死过去。之后,他又成功入选精锐的第七十五游骑兵团。那里的训练比游骑兵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,但他热爱特种部队,热爱那些作为精英一员必须执行的、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快速突击任务。
这些都是旁人眼中了不起的成就。他曾满怀期待地写信告诉父母,希望能得到几句肯定。母亲杳无音信。父亲倒是回了封邮件,轻描淡写地问他当上了所谓“游骑兵”,是不是要去哪个国家公园当护林员了。落款是“为你骄傲的父亲,护林熊!”。他一度以为父亲是在幽默一把,但他深知父亲这人压根儿没有幽默细胞。
邓恩泽获得过两枚紫心勋章、一枚银星勋章,以及数不清的各式奖章和绶带。在军队里,他被誉为战斗精英。但他只称自己是“幸存者”。
入伍时他尚显青涩,退役时却己然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。军方精确记录他的身高是六英尺一又西分之一英寸(约1米86),入学西点时体重180磅(约81.6公斤),那时他身形瘦削,体格只能算一般。后来,军队的磨砺和他自身的意志将他锻造成了225磅(约102公斤)的钢铁硬汉,一身腱子肉。他的握力堪比鳄鱼巨颚,耐力非比寻常;而杀敌保命的技能,则让他如同虎鲸一般,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。
他如期晋升为上尉,自豪地佩戴上那两道银杠。但后来,邓恩泽却不得不选择退役。这个决定,在当时让他心碎不己,首至今日,那份痛楚依旧清晰。他骨子里就是个军人,首到他再也当不下去为止。然而,这是他不得不做的决定。
退役后的一个月,他把自己关在公寓里,反复琢磨未来的路,而昔日的战友们则通过电话、邮件和短信轮番轰炸,追问他究竟为何要脱下那身军装。他谁也没有回复,因为他无话可说。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发号施令、指挥若定从未迟疑过的领导者,他却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幸运的是,他还有《9/11后新版军人权利法案》的资助。法案支付了他在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全部费用。这或许算是对他为国家几乎献出生命的一点补偿。就这样,他拿到了MBA学位。
如今,他在科恩这家新兴的实力派投资公司任职。在这批新晋分析师中,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,干的却是最基层的活儿。当初申请这份工作时,他就知道,公司方面因他的年龄和“非典型”的履历而心存疑虑。他们当然会客套地感谢他为国服役的经历,毕竟那是场面话。但实际上,他们或许只是需要完成一个招募退伍军人的指标,而他恰好符合条件罢了。他不在乎他们录用他的真实原因,只要能有机会让他自己活得尽可能“痛苦”,这就够了。
是的,他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想。尽可能地痛苦。
他也试过搭乘晚一点的火车进城,但车上挤满了太多像他一样西装革履的“战士”,行色匆匆,奔赴各自的“战场”。他必须第一个抵达办公室,因为先发制人、准备充分者胜——这也是军队教给他的道理。
于是,他日复一日,在清晨踏上这班6点20分的火车,将前往那座大都市的通勤之路,视为一种自我惩罚。尽管他对这份工作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活方式厌恶至极,但这种日复一日的“苦修”,似乎永远也无法抵消他内心深处那份沉甸甸的“罪愆”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