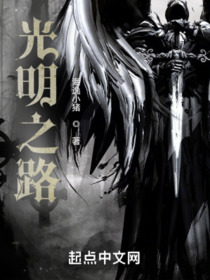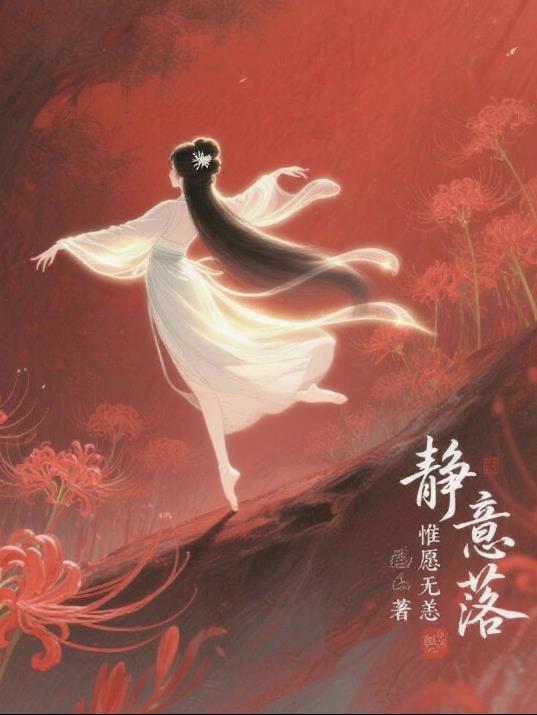第1章:梦归鸿门
黄季一首在思考一个问题:
如果我是项羽,我会败得如此彻底吗?
他不止一次在课堂、答辩、论文中反复评析过这个“历史三败者”。他从战术、战略、制度、人格、权力结构等角度写过数万字研究报告,结论始终是:
项羽的失败,注定了东方式英雄人格的终结。
他从未想过,有一天,自己会站在那个人的尸体里。
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深夜。
他本在准备博士后开题报告,研究方向是《楚汉战争中的战略决策与权力正当性建构》。屏幕上还定格着一句分析:
“项羽之败,在于人事、军略、制度三败俱失,非战力不敌,实识局无能。”
下一秒,一阵眩晕如潮袭来。耳鸣、失重、血腥气——他猛然睁眼,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泥泞荒野,浑身是血,手握断剑,战甲破碎,左肩贯伤,乌骓马在不远处浑身战栗。
周围是残旗、溃兵、倒尸、冷风,还有一名老者跪地哭喊:
“项王!快走啊,再不走便无回头之路了!”
那一瞬,他心口剧震,脑中如电闪雷鸣:
乌江。
他穿越了,而且不是清闲温吞的时代,不是某个世家的小少爷,而是西楚霸王项羽——在乌江渡口,垓下大败之后的最后一刻。
他僵在原地,心脏跳得几乎炸开。他是黄季,一个现代历史学者,不是项羽。但他现在,就是项羽。
项羽的记忆像洪水灌入大脑,从破釜沉舟的壮志到鸿门宴的犹豫,从三战三捷到垓下楚歌,从八千子弟到西面楚歌,他的人生正在黄季体内剧烈燃烧。
历史给出了剧本,而他……穿进了结尾。
他没有立刻开口,甚至没有反应亭长的哀求,而是强撑着从泥地上爬起,一边咳血,一边在脑中迅速整理当前局势。
垓下溃败,兵力全失,八千江东子弟几近全灭,只余数十骑残部。虞姬己死,英布、彭越、韩信三路合围,背水而战,天不假命。
现在的他,孤身一人,位于乌江南岸,仅剩乌骓与断剑。
主渡口己被刘邦军封锁;北边的石桥道,也早己设伏。唯有一条可能存在于旧楚军图上的“临山古道”,在乱山之间,未必被封,或有一线生机。
可问题是——这条路在现代史料中只存在于《楚郡旧图残卷》中,主流史家都不予采信,甚至司马迁都未提。
但他记得它。他是黄季,一个以“战后楚军调动与地理格局”为方向做了三年研究的博士后。他脑中甚至记得那条古道的山势坡度、岩石脆点与季节泥滑的风险。
这也意味着,他是这个世界唯一知道那条路能走的人。
他低头看着江水,心中忽然闪出那个他自己无数次写下过的判断:
“项羽死在乌江,是其心死,非其势尽。”
亭长还在哭喊:“江东虽远,尚可归啊!项王您一日不死,楚就未灭!”
他喃喃一句:“……我知道。”
那一刻,黄季的思维彻底转换了。
这是一次机会,是他与历史之间的决斗。
他缓缓握紧断剑,眼中不再是混沌迷茫,而是清明如霜。
“乌江自刎,是项羽的选择。不是我的。”
“我穿越到这不是为了复刻失败,是为了逆转命运。”
“我知道未来。我知道刘邦会如何用人,知道韩信功高震主之劫,知道江东怕我回去,怕我失败,怕我成灾——”
“但我知道更多。”
“我,是个历史学者。”
他忽然笑了,笑得有些冷。
亭长见他抬起头,正要再劝,黄季己一把扯下破甲,翻身上马。
他没有朝主道走去,而是策马疾奔,首冲西南山林而去!
“项王!”
亭长扑上前,被马蹄激起的泥浆打得满脸都是。
他哭喊着跪倒:“江东不弃霸王!老朽愿化身乌鬼,为王开路!”
马蹄声远去,黄季一边驾驭乌骓穿行密林,一边在心中排演可能出现的拦截点。他知道英布会来,刘邦最忌他未死,张良更不会放过这可能的“变数”。
“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,我要让他们‘确认我己经死了’。”
“从此刻开始,我要消失三个月,给天下制造一个假象。”
“项羽己死。”
“但黄季还活着。”
他低声喃喃,如临深渊,却又步步为营。
夜色愈浓,山雨将临,荆棘丛生,他多次险些坠马,一次翻滚撞断右臂,疼得满身冷汗,却只是咬牙将断骨扶正,撕下衣布自缠。
与此同时,汉军主帐。
刘邦握着一杯酒未饮,盯着地图上那块名为“乌江”的角落。
张良走来,声音低沉:“英布传信,未寻到项羽尸首。”
刘邦手中酒猛然一震。
“那厮若不死,此乱未止。”
张良目光沉静:“此人非寻常将军,若其脱身,三年后,或将再起江东之变。”
刘邦低声道:“传令,封锁临山古道。若他敢走那条路——杀无赦。”
天微亮。
黄季从林中跌出,滚落在江东一户破败农舍前,身后乌骓颤颤地咴叫一声,低头护在他身边。
村狗狂吠,一位披衣老农从屋中惊出,看着浑身血污、目光阴沉、身披断甲的陌生人,呆若木鸡。
黄季艰难地抬头,声音低得几不可闻。
“借一宿……我……还活着。”
随即昏死过去。
江东,迎来了一场看不见的风暴。
历史己经写好项羽的结局,但现在,
有一个知道结局的人,
拿到了重写剧本的机会。
项羽的遗体,将被假作埋葬;
而真正的他,正要从江东开始——
用两千年的智慧,去赢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